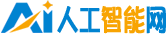有人問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是什么歌(當女生不回復你消息的時候)
跟女生聊的時候,對方不回復心里就百感交集了,隔一段時間男生就發一條消息,一直這樣發下去,直到女孩子把自己拉黑了。在這個過程中你每發一條消息,其實就是在降低你的價值
本來沒什么事情的,女生只是去忙了,沒時間回復,結果你就被自己的焦慮情緒給搞砸了,永遠的失去了這個女生
面對這樣等待的焦慮,我們應該怎么應對呢?
一. 看女生回復自己的速度,也許她只是暫時不回復,過個幾個小時就回你了,這個時間你就可以選擇去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情,而并非花在這上面
在隔個幾個小時之后,看看情況,男生要學會隨機應變,撩妹并不是用死的方法,都是要看實際情況行事
二. 如果看到她好幾天都不搭理自己,那么你應該思考一下她是不是去撩別的男生了,做好心理準備,我們男生往往都覺得女生是一對一的跟自己聊天
實際上女生身邊的男性多了去了,每天問候她的人數都可以排成一個長隊,所以你只是她身邊的一個追求者而已
知道了之后那么你該做的不是接著去找她,而是去發一些吸引女生的動態,比如有價值的聚會,有意思的野炊,吊人胃口的美食,惹女生母愛泛濫的小寵物,接著不用你去找她,她自然會主動點贊和評論你的朋友圈
三、 如果是在睡覺之前和女生聊著聊著不理你了,那就是她不想去回復你,永遠不要相信女生可能睡了,去忙了這些理由,女生大晚上都很無聊的,而且幾乎都是夜貓子
沒個一兩點,很少睡覺,所以她肯定是拿著手機和別的男生聊天,她不回復你是因為對你興趣低,或者你聊天聊崩了,那么你就該選擇睡覺
第二天她如果找過來,就接著聊,沒有的話也不必焦慮,當你擁有那么多追求你的異性,你也一樣會不在乎某些女生的消息。
最后的建議是,男生應該多和一些不同的女生聊天,多去增長自己的見識,不要只和一個女生一對一的聊天,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平衡的事情。
曾經的我追女生也是一竅不知,愛上一個女生,天天陪她聊天,哪怕自己不喜歡熬夜也陪她,她想要什么我都會買給她,衣服包包什么的,
花了也快五千元了,但是換來的只是她的一句:“你人很好,我們還是做朋友吧。”
她身邊的一個追求者,就跟她去約會嘛,然后去吃了一個不過百的飯,就把她拿下了,那時候我真的不懂。
我幾乎快崩潰了,我被徹徹底底的掛上了備胎俠的稱號,這是多么諷刺,
就這樣我在渾渾噩噩的過了幾天之后,在上,不是有公眾號嗎,
就在 “西施江湖” 上關注后看到了導師為我分析上說的“追女生不是靠跪舔,而是吸引,讓妹子主動過來。”
里面的兄弟都是約妹子讓妹子自己過來找你約會,心甘情愿,而不是你去追逐
我開始看它的文章,漸漸的改變自己,形象,氣質,聊天技術,還有對女生的姿態,如何吸引,做展示面,價值展示等
原來自己并不是沒有得到女生,而是在女生面前丟失了東西。
而丟失的東西,其實就是男人的姿態,本該有的姿態,自己在追求的過程中變成的是跪舔的狀態。
想看的兄弟可以去搜索公眾號: 西施江湖 (搜索完后記得要點關注,不然看不到文章)
這可未必說實話,得分人。
筆試成績上點心,大部分情況下,面試前可以知道。對于筆試成績,如果小伙伴們能夠自己上點心的話,大部分情況之下,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個別情況,我說的是大部分情況之下,我們都可以知道的。
一是,我們在進行資格復審的時候,會有一些簽名確認的表格和名單,這種情況之下,我們在簽名的時候不要傻乎乎的,只是簽自己的名字,眼睛靈活點簽名的時候用眼掃一下,看看這個名單上有沒有自己和同崗位考生的分數。因為你們同一個崗位,名字表格肯定都是挨在一起的,大部分情況之下,資格復審的時候是可以瞄到筆試成績的。
二是,在面試之前,大多數單位都會在網絡上發布一個進入面試的名單,然后這個名單有的會考前一周發布,有的會考前2到3天發布,甚至有的會考前的一個晚上發布,一般來說都是會發布的,那我們就要關注這個名單,名單上面一般會有同崗位成績的分數。
三是,大家目前網絡信息這么發達,肯定有會會有一些交流的地方,那小伙伴如果有心的話,也可以去加入一下這些信息交流地,說不定還會找到你的同崗位考生,但是這種情況之下,人家說不說實話就不一定了。
一般考生都會說實話。其實我們大部分小伙伴還是比較單純善良誠實的。當然換位思考,如果我是面試的小伙伴,別人如果問我筆試考了多少分,我應該不會隱瞞或者是欺騙,因為已成定局了,是改變不了的呀,說下又何妨?而且我們大部分小伙伴很多都是剛從學校里面出來,很多都是比較單純,所以一般都會說實話,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特殊情況,因為有的人他是保護意識比較強,或者是不愿意跟別人說,這也是有例外的。
也有少數不說實話,且欺騙別人的情況。其實不僅僅是筆試成績,有時候如果面試成績不是當場公布的話,部分考生他都不會告訴自己同崗位考生自己的真實情況的。
今年帶省考的時候,有位考生他面試的時候就是沒有當場公布成績,他是第一個面試的,然后他面試完之后在考面等同崗位的兩個考生面試完,那其中第一個出來的崗位排名第三的考生呢,特別熱情,給他看了那個面試成績單,很淡然的跟他說,哎呀,你考的比較高,恭喜你啊,你贏了,我回去再繼續加油。
但是后面出來的第二的考生,由于他們分差比較小。當時那個考生看到我這位學生在外面等他的時候,表情就不是特別的好,然后我這位學生問她成績的時候,她也沒有說,反而非常老練的反問了一句,你考了多少?那我這位學生也是比較沒有心機的,就直接把自己的分數說了出來,然后當時那個第二名的臉上就有點發綠。然后就沒好氣的說了句你上了,但是因為我這位學生之前在網上看到過很多欺騙分數的案例嘛,就想問問說你考了多少分,然后那個人就沒好氣的氣急敗壞的走了,所以當時一直到面試成績出來之前,而這位考生他都是非常忐忑的。
理解心情,但要淡然。其實我非常理解大家等成績這個焦慮的心情,就好像有一位考生說的,不管考上考不上,早點告訴我們,讓我們心里有個數兒,考上了,就好好高興,考不上就趕緊去準備別的考試或是找工作。
但有時候等待也是我們修煉人生的一個過程,必要的等待,也是值得和需要的。
被已經是一個足以讓自己背負一輩子陰影的夢魘,怎么可能還會把自己恨不得永遠忘記的事情再描述一遍?這跟再次被沒什么區別!所以說絕大多數都是假的,或者說都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!
網上看到的各種女性被的經歷,要么是像寫小說一樣瞎編的情節,要么是根據自己知道的事情進行編寫,目的無非兩種,或博人眼球獲取流量,或利用事件教育大家注意防范;但無論出于什么目的,請各位在編寫之前一定要征得受害人的同意,以免再次傷害到她們。
當然也不排除有受害者用自己的被侵犯的前后經歷書寫出來,幫助更多女孩避免受到同樣的傷害,這是真正堅強、正義、無私、大愛的女孩,但不會多,極少數。
也有可能是受害人迫于某種外界壓力現實中不敢報警,利用網絡來表達一下自己的經歷、想法,看到此類文章,請多關注一下,說不定就可以幫助她!
我見過的渣女,她的故事能拍一部電影,還是懸疑恐怖片,就是我一個同學。上學時這同學漂亮但挺老實的,父母長年外出打工,跟著奶奶一起生活,畢業后沒有消息了,直到出事才知道有關她的事跡!
很多渣女是玩夠了瘋夠了,回來找個老實人嫁了。可她非要玩刺激的,事情是這樣的。
她高中畢業后外出打工,因為他長相和身材比較好和明星柳巖有點相似。后來接觸社會上的人越來越多,經常出沒高檔高消費場所,后來就在廠里待不住了,至于后來做什么工作不清楚,有人說是酒吧坐臺等等。
混了十來年也沒結婚,最后父母給他找個男的,是個程序員工資挺高的,問人家要了三十萬彩禮,就結婚了。結婚后女的不讓男人回家,過年回來大年初二就讓他出去上班賺錢,他老公工資卡都在她手里,他老公每月生活費都要問老婆要。他人老實,心痛老婆,事事都聽她的。
她在家里還明目張膽的把以前男人帶會家,拿他老公的錢養以前的小混混。有次被她婆婆撞到了,還把婆婆打一頓,頭發快給拔光了。程序員回來跟她吵鬧,她不但死不承認,還把他也打個半死。程序員也不敢往外說,家丑不外揚。只要她照顧好孩子,他也忍了。以為真是誤會了。這事過了以后,這女的很大膽了,一年至少在別人家過半年。孩子丟給婆婆,自己去找野男人。她老公的工資都被她花的一個不剩。
最讓人受不了的是,這十年里她生了兩個孩子,老大是正常孩子,是個腦癱兒。兩個都不是程序員的,生的時候程序員感覺時間對不上,她就找各種理由搪塞,程序員就偷偷做了鑒定,果然不是親生的。找她理論她不但沒有內疚感,還出口狂言說“我這么漂亮嫁給你是你的福氣,跟你明說吧把,老大也不是你的,就是現在離婚我馬上就能找到下家,可你呢”?這話把他氣的直撞墻,這么多年辛苦白費了,對孩子付出的這么多感情,最后都不是自己的。爭吵也沒個結果,他老婆就走了。
兩個孩子都不管,去了相好的家里,不露面了。剩下兩個孩子程序員管又不甘,不管又不忍心。到處找她下落,最后知道地點,找她就是想讓她把兩孩子帶走,從此一刀兩斷。可她就是不愿意,說自己沒有能力扶養,孩子親生父親她也不知道是誰。爭來爭去就打了起來,程序員哪里打的過她,何況還有她情人在場。他也是被打的急紅了眼,拿起桌上的菜刀就亂砍,把兩人都砍死了。最后被判了15年,由于兩個孩子找不到親生父親也是由程序員媽媽照顧。
你說這女的是什么心態,怎么會這樣,一點自尊、良知不要,近乎變態惡心的行為害了自己不要緊,還禍害了好好的一家人。這個后果也是她最好的歸宿了。只是苦了兩個孩子和程序員了。
2017年,我記得那是青島天氣正熱的時候,應該是8月份,那天晚上海邊還是比較涼爽,我和丁一炒完菜,要了一桶扎啤,放開了喝。又從外面要了燒烤,兩人邊吃邊喝,不一會就起來上次廁所,一桶30多斤的啤酒幾乎喝光。
記得好像是快十一點了,丁一接到了一個,是他的表哥打來的,他表哥是個警察,表嫂在醫院上班。表哥讓他立刻去她家。
我見他喝得醉醺醺的,就勸他別去了,去了說不定更壞事,沒想到他說了一句話,直接把我驚在原地:“不去不行,于得水,我表嫂來說,說……她家里多了個人……”
我和丁一趕到她家,見到了他的表哥陳正和表嫂范麗麗。
范麗麗對我和丁一講起了剛才發生的事:昨晚范麗麗和陳正都上夜班,范麗麗十點下班,陳正十二點下班。范麗麗上班很累,回家后就開始洗漱,洗漱的時候發現老公的鑰匙忘在洗手臺上,不禁埋怨丈夫粗心大意,接著把鑰匙放進抽屜,就去臥室睡了。
睡得迷迷糊糊的,聽見外面敲門,范麗麗知道老公回來了,就去給他開門,屋里有幾盞小燈亮著,光線昏暗,范麗麗實在太困,只看了個輪廓,就返回臥室里躺下,過了一會,那人推開臥室門進來,也沒和范麗麗說話,在旁邊背對著她躺下了。
睡著睡著,范麗麗又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,起來一看,老公沒在床上,就走到客廳,問了一句:“誰?”門外陳正回答:“是我。”范麗麗開門就埋怨他:“你不睡覺,出去干什么了?”陳正聽完她的話,一愣,對范麗麗說:“我這不是剛值完班回來嗎?”范麗麗大吃一驚,問::“你確定剛才沒回來?”陳正:“我啥時候對你撒過謊?”兩人把事情一對,一股涼意從腳底透上來,趕緊查看了一下,家里的財物也沒損失,又立刻去查看了樓道里的監控視頻,看到了令人驚悚的一幕::敲開陳正家門的不是一個人,而是一身衣服……
那身衣服像被人穿著一樣走到門前,敲了敲門,范麗麗打開了門……
兩人看完,驚駭的都說不出話來。
丁一問陳正:“哥,最近你這邊有沒有什么異常?”
陳正想了一會,說:“沒有什么特別的。”但我分明看見他對丁一使了個眼色。
丁一給陳正幾張符,讓他貼在門,玄關,和床頭柜上,關門休息,然后準備告辭,回飯店。陳正一直送下樓來,等到了樓下,他叫住了丁一:“丁一,有個事我不敢守著你嫂子說,說了怕她害怕……”他頓了頓,指著樓后面,接著說:“這座樓后面是一片拆遷區,那里有一座騰空的房子,房子旁邊里有一口多年的水井,原來的時候村民都吃里面的水,這個月我上夜班,十二點下班,好幾次我在廚房弄吃的,都看見,有一個女人穿著一件連衣裙,走到井邊,朝井里看……”
丁一皺著眉頭,對陳正了一句讓人毛骨悚然的話:“從種種跡象來看,你家里應該藏著一件尸衣……”
陳正當時就否認:“絕不可能,我家的衣服你嫂子不長時間就扒翻一遍,怎么會有那個?”
“這件事有點蹊蹺,明天我過來仔細看看什么情況,你和嫂子都不要去上班。”
2
第二天,丁一叫上我,一塊到了陳正家,和陳正,范麗麗細細的拿出衣服查找一番,結果什么也沒發現。
快到中午的時候,飯店經理打來,讓我們回去上班炒菜,我和丁一就回去了,臨走給表哥三串桃木手串,讓他們和女兒每人戴一串,還叮囑晚上不要忘了帶鑰匙,看看情況再說。
幾天后的一個上午,范麗麗又打來,讓我和丁一立刻過去。
趕到她家,只見她和陳正坐在沙發上發呆,女兒想必送去學校了。
穩了穩神,沏上茶,兩口子結結巴巴的說了最近發生的一切:這幾天一直沒什么異常,工作也很辛苦,昨天晚上,陳正沒去值班,在家里早早吃完飯,出去遛了一圈就回家了,看了會電視,9點多,范麗麗也下了班,兩人熄燈睡覺。
也不知睡了多久,陳正醒了,醒了一看,十二點,起來去了趟廁所,習慣性的去后陽臺看看,慢慢的遛達到廚房,透過窗戶向那邊看,沒看見有人,就準備回去繼續睡,可是一轉眼,就覺得不對,再定睛一看,大吃一驚:那個披肩發穿連衣裙的女人竟然朝他們的樓棟走,并且已經快走到樓前了……燈光昏黃,看不清長什么樣。
陳正手足無措,呆呆的看著她消失在視線里。
回到臥室,范麗麗還在熟睡,也沒告訴她,一個人翻來覆去睡不著,到快天亮了才迷糊了一會。
起床的時候,陳正還是把事跟范麗麗說了,本以為會嚇到范麗麗,所以還遮遮掩掩的,沒想到范麗麗對他說的更加驚悚……
范麗麗做了一個奇怪的夢,夢見一個看不清面孔的女人在家里走動,在客廳坐了一會,去衣櫥找衣服。范麗麗人嚇醒了,但是身子動不了,接著聽見一陣喘息聲,好像是和她對著鼻尖看她,還聞到一股來蘇水的味道。
范麗麗嚇得要死,想動動不了,想喊喊不出,一直到天亮才恢復正常。
兩人立刻決定,讓丁一過來。
丁一聽范麗麗說完,沉吟一會,問她:你聞到有來蘇水的味道?范麗麗點頭。
丁一:“醫院不都是用來蘇水消毒嗎?你聞到來蘇水味也不奇怪啊。”
范麗麗說:“我們醫院早就不用來蘇水消毒了,現在都用84消毒水。”
這時,陳正插話了:“誒,你說什么?來蘇水?”三人都看他,范麗麗說:“對啊,我聞到就是來蘇水的味道。”
陳正說:“這就怪了……”
欲言又止,范麗麗看他一臉茫然的樣子,急了:“有啥事快說!別拉一半留一半。”
陳正白了她一眼:“昨天早上,前街有個私人診所的大夫去報案,說是他的診所失竊,錢沒少,貴重的藥也沒少,唯獨少了兩瓶來蘇水……”
幾個人的的腦子轉不動了,無法理解,這事實在是太離奇。
丁一:“看來這事沒那么簡單了,我得去找個人幫你們看看。”
范麗麗連忙答應,讓丁一幫忙解決,越快越好。
我和丁一從他家出來,丁一開車,直奔城陽區。
在路上,我問他:“這事也忒不靠譜了,你表哥以前不是住的好好的嗎?怎么就突然發生這么多事?”
丁一一句話讓我如墜冰窖:“這不是剛過了七月十五嘛……”
3
等到了地方一看,就知道丁一找的人肯定不一般。
城陽區勞務市場人頭攢動,熙熙攘攘,不時有車停下,人群哄的圍上去,又哄得散開,討價還價成了主旋律。青島人對金錢普遍很仔細,很計較,就算是翁婿打麻將,欠賬也不會超過3把,否則大家臉上都不好看。
丁一領著我在人群里穿行,尋找他要找的那個人。
這時一輛車停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,只見人紛紛朝那邊圍過去,有幾個甚至撒丫子往哪跑。
我和丁一也湊過去看熱鬧。車主開了一輛帕薩特,找幾個工人往他家樓上搬家具,男工,出價180元一天。三四個勞力扒在他的車窗上,要求他220元一天。這時候別人都不出聲,如果有出聲的拉低了價格,那就是壞了規矩,是要被唾棄的。
僵持了一會,帕薩特啟動要走,往前面去找人。
突然聽到一聲大喊:“130!我去!”
所有人的目光對準了喊話的人,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,花白頭發,亂蓬蓬的。穿一雙解放球鞋,綠粗布的褲子,一件保安的上衣不知從哪兒撿的,好像是一個從70年代穿越來的人。臉上也沒幾兩肉,胡子拉碴,手脖子上竟然有紋身,紋著一顆心插著一支箭。唯一讓人不討厭的是衣服還算干凈。他剛喊出130,氣的旁邊的人一把把他推了個趔趄。他并不生氣,還咧著嘴笑,帕薩特也沒搭理他,往前走了。可能是怕他起哄。丁一戳了戳我:“于得水,就是他。”
我張開嘴合不攏,驚訝之余,問出一句沒頭沒腦的話:“你怎么不找楊姨?”
丁一:“楊姨去南方拜菩薩了。”他可能是感覺出什么:“千萬別小看人,這個人可是了不得。”
鬧哄哄的人都散去了,丁一領著我找到了他:“張嘴就讓我吃驚不小:“師爺……”,老頭攔住了他:“千萬別這樣叫!叫我老袁。”丁一拿出一條哈德門煙,遞給了他。
老袁嘿嘿一樂::“這還差不多。中午算你的。”
三人說了一會話,就一塊進了勞務市場旁邊的一家飯店。
老袁要了六個菜:生拌茼蒿,糯米藕,清炒山藥,拔絲地瓜,大盤雞,火爆螺片。這家飯店的糯米藕和大盤雞還是做的很地道,特別是大盤雞。
我原來做過大盤雞,但是沒有他做的好吃。先用八角花椒煸鍋,放入蔥段,炸至黃色,烹入醬油。放入姜片(姜片不宜煸鍋,有致癌物。)將汆過的公雞塊倒入,放生抽提鮮,老抽提色,放入砂仁,白芷,肉桂,丁香適量,倒入一暖瓶開水,大火收汁,差不多的時候改成小火。直到收的湯汁濃稠,出來的雞肉必然是嚼起來咔哧咔哧的發脆。而不是跟土豆一樣的面。注意中途萬不可加水,否則就不是原汁原味。三人一邊吃著,丁一一邊把事情跟他說了。
老袁一邊聽一邊點頭。一盤雞讓他干掉一半多。最后還把沒吃完的打包。
從飯店出來,丁一去開車,老袁用牙簽剔著牙,心滿意足的拿出了煙。丁一開過車來,我上了車,丁一松開了離合器。老袁不緊不慢的點上煙,叫住了丁一:“哦,對了,你把這個拿上。”說完從口袋里拿出一副眼鏡,看樣子好像是老花鏡,遞給丁一:“把這副眼鏡平掛在客廳門的門套上,我看看是什么東西。”
說完,急匆匆的往勞務市場那邊趕去,剛剛又有輛車停在那里找人干活。
我滿腹的問題想問丁一,丁一已經看出了我的疑惑,輕輕一笑“自食其力,他是在修行……”
我說:“修行,去看大門也行啊,非得在勞務市場混。”丁一啞然失笑。
4
下午,我和丁一返回陳正家。跟兩人一說,兩人聽說有這么一個奇人愿意幫他們,心情也不張了。
陳正搬來一個凳子,拿出兩個鋼釘釘在墻上,把眼睛端端正正的掛上。
說了一會話,我和丁一就告辭回飯店了。
第二天一早,范麗麗又給丁一打來,聲音里帶了哭腔:“丁一,昨晚又夢見那個看不清臉的人了……”
丁一一直安慰她,掛了,丁一打給了老袁。老袁全名叫袁修成。
接通,老袁說話磕磕巴巴:“丁一,啥……啥啥事。”丁一在里把事一說,最后加上一句:“大早上起來喝的啥酒!”老袁一句話把丁一氣樂了:“我還把你的事忘了來,等一會。”沉默了一會,老袁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:“在臥室東墻里面……”說完就掛了。
5
我和丁一立刻趕往他表哥家,跟陳正一說,二人頓時傻眼。商量了一下,陳正決定和物業溝通一下,拆開臥室東墻。結果物業不同意,說是承重墻。最后沒辦法,只好先打一個小孔看看究竟有沒有丁一說的東西。結果,剛用沖擊電鉆打進去不深,一件碎花的衣服就露了出來。范麗麗直接哭了,自從買了這套二手房,一年多了,沒想到一直睡在這東西的旁邊。
但讓她沒想到的是,讓她哭的事情還在后面……
隊的人來了以后,找來了工人,對墻壁進行破拆,因為是承重墻,破拆面積不能大了,拆完后還要立即修補好。
一具頭朝下的女尸露了出來。已經白骨化,頭部離地面大約六七十公分,范麗麗欲哭無淚:女尸的頭部,離她睡覺時的頭部,僅有不到30公分。臉對臉睡了一年多。據隊的人說,還有一件事情更讓人匪夷所思:女尸身上竟然有一股淡淡的來蘇水味道…
范麗麗和陳正搬到陳正父親家住,陳正也去局里找辦案的同事打聽情況,女尸的身份還在核實中,暫時沒有結果。
范麗麗心情不佳,整天心里好像堵了一塊大石頭。晚上做的夢就像是一卷快進的錄像帶,尖叫,雜亂的人影,竊竊私語,喘息聲,追逐,亂七八糟,第二天醒來也記不清什么內容,就是害怕和難受。
給丁一打說了情況,讓他找師傅給解決一下,丁一撥通了老袁的,問他在哪兒,想過去找他。老袁嚼著檳榔,慢條斯理的說:“這事我不能管……”丁一懟他:“平常又要煙,又要酒,得空還吃吃喝喝,關鍵時候掉鏈子是不?”老袁嘿嘿一樂:“到時候你就知道了,這里面有因果……”說完徑自扣了,再打也不接了。
丁一無奈,只好給楊姨打去,楊姨說不了解情況,不好出點子,但是可以先送一送。有什么情況直接告訴她。
當天晚上十點,丁一畫了一張符,燒掉,放進一碗涼開水,兌上一指甲蓋朱砂,讓范麗麗喝下去,丁一嘴里念念有詞,燒了幾張燒紙,點了三炷香,雙手高舉,讓我和范麗麗拿著燒紙,三人出了陳正父親家,走到了最近的一個十字路口。
丁一把香插在路邊,又對空說了幾句,拿過燒紙去,折了一段樹枝,畫了個圈,把紙放在里面,用打火機點著,用樹枝挑弄著,燒完,對我倆說了一句,“都別回頭,一直往回走。”
三人往回走,我是不敢回頭看,但走著走著,就有了一種怪怪的感覺,不由自主的斜著眼往后看,頓時覺得渾身冰涼:我看見了一塊碎花裙子……
回到家里,范麗麗臉色煞白,緊張的說不出話來,丁一給她倒了一杯水,關心的問她是不是身體不舒服,范麗麗嘴唇哆嗦,結結巴巴的說:“剛才往回走,我……我……我聞到一股來蘇水味……”
丁一立刻給楊姨打去,楊姨聽完,說:“這事挺麻煩,她和她在一間臥室里呆那么長時間,她對范麗麗很熟悉,想分開她倆很困難。這樣吧,我快遞回一串項鏈去,讓范麗麗戴上,她就不敢近身了。”
說完又加了一句,把我嚇得差點沒哭了:“你倆小心點,別讓她跟上了……”
煎熬了兩天,楊姨的項鏈快遞過來了,就是一串小珠子的項鏈,唯一不同的是,項鏈頂端墜了一顆狼牙。
聽丁一說,那是一顆百年狼牙。
第二天,范麗麗打來,說昨晚休息的很好,丁一也算松了口氣。
范麗麗在里接著說,希望能花錢買楊姨的那串項鏈,丁一笑了:“這是楊姨驅邪避煞,多年修煉的利器,會賣給你?她這兩天就回來了,耐心等等。”
當晚,她兩口子邀請我和丁一去他家吃飯。
在飯店忙活完,已經是8點多了,兩人開車直奔陳正家。
陳正準備了很多菜,陳正的父母和范麗麗一塊作陪,六個人邊吃邊聊天,一直吃到接近十點。
最后要散席的時候,陳正問丁一:“弟弟,那天我在樓上的時候,半夜看見那個女人朝井里看是怎么回事?你覺得正常嗎?”
丁一想了一會:“這個事說不準,或許是個神經病,但是神經病的話也太奇怪了,不可能一連幾天都去啊……”
陳正:“要不咱們現在沒事,過去看看,無論是什么情況,也算是解開我心里的一個疙瘩吧。”
幾個人一起看向丁一,他想了會,同意了,喝了點茶水,叫著我一塊準備前往拆遷的現場。陳正的父親不放心,非要一塊去,陳正好說歹說,老頭也不聽,只好帶上他,一塊去現場。
四人驅車趕到那里的時候,是十點半多點。四人下了車,步行前往。
還沒到那口井,我就覺得頭皮發麻,心跳加速。
四人拿著兩只手電,燈光晃來晃去,趕到了井邊。那是一口廢棄了的井,井里也早就沒有水了,本來拆遷的人準備填掉它,可是不知為什么沒有,可能是停工了,沒來得及填。
丁一和陳正的父親一人一只手電,往井里照,四個人趴在井口往里看。
井還不淺,看不太清楚,隱約能看見有很多垃圾,有紙,方便袋,石塊等等,看了一會也沒什么發現,起身準備離開,突然丁一驚呼一聲:“那是什么?”
我心頭一緊,看向丁一用手電照著的地方。
陳正和父親也一塊往里看,只見一雙紅色的繡花鞋規規矩矩的擺在井底,像是有個女人剛剛脫下來,擺在那兒,然后離開。
陳正不以為然:“就是一雙扔了的鞋子,大驚小怪的。”丁一搖搖頭:“不像扔的,像是擺在那兒的,扔的話扔不了那么整齊啊。可能有什么說道,明天我問問楊姨。”四個人又往井里看了一會,再沒有別的發現,就打算往回走。
四個人陳正的父親拿著手電筒在最前面,依次是我,丁一,陳正,順著拆遷后高低不平的小街往回走。
我和丁一邊走邊聊,天上一輪彎月,朦朦朧朧的,小街上沒有燈,路比較難走,離有燈光的地方有一百多米,四人走著走著,丁一拽了拽我的衣服,說了一句:“于得水,等一會,情況不對。”我回頭看了看他問:“怎么了?有什么不對的?”這時陳正的父親也停下了。回過頭看。
三人不約而同大吃一驚:陳正不見了!
不知什么時候,路上只剩下我們三人。
丁一叫了一聲:“哥!”沒有人回答。
陳正父親急了,連聲叫:“陳正!陳正!你在哪兒?快出來!”我也一塊叫陳正的名字。
可是沒有用,陳正就像人間蒸發了。折騰了一會,才想起來,趕緊給他打。
丁一撥了他的手機號,打通了。
丁一按了免提鍵,只聽見手機里傳來一陣沙沙的電磁干擾聲,和滴水的聲音。丁一遲疑了一會,問:“哥,你去哪兒了?”手機里傳來陳正的聲音,好像很遙遠,又跟微弱:“丁一,我也不知道在哪兒……”接著又說:“看不清楚,一個大房間,什么也沒有,黑漆漆的。”
丁一:“你快出來啊”陳正:“嗯……”停了一會,陳正又說:“這個房間沒有門……”
丁一不知說什么好,陳正又在里說話:“咦,這里有雙鞋……”接著手機掛斷了,再打過去,就只有忙音了。
當晚,110也來了,幫忙找人,怕范麗麗和陳正的母親擔心,沒告訴她倆。
手電筒,手機,所有能用的照明設備全用上了,沒發現陳正一絲一毫的痕跡。
接著打他的,倒是能打通,但只能見遠遠的,一個女人唱歌的聲音,時斷時續,令人毛骨悚然……
整整找了一晚上,一點頭緒也沒有,第二天一早,丁一決定立即去找老袁,我倆驅車趕往城陽老袁的住所。老袁租的是一間地下室,一個月120塊。
等到了老袁的住所,鐵將軍把門。再去勞務市場找他,又沒見到他的人影。丁一恨恨的說:“這老家伙躲著咱們。楊姨今天晚上回來,等她回來再說吧。”
忙活了一晚上,都很疲憊,但是一點睡意都沒有。趕到老陳家,范麗麗和陳正的母親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,兩人情緒都有點失控。陳正的母親更是哽咽著,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。
7
終于熬到晚上,我和丁一早早地就趕到了火車站接楊姨。
等到楊姨從車上下來,也顧不上多說話,直接上了車,一路飛奔。在車上,我簡單的和楊姨說了一下情況,楊姨皺緊了眉頭。看的出來,她也很疑惑。
只聽她喃喃自語:“這事也忒怪了。”我問楊姨:“是不是上了身,或者是被迷了魂?”楊姨說:“好幾種可能,這并不是讓人感到蹊蹺的,我主要是考慮老袁說的那句話,這里面有因果……袁師傅說的話看似輕飄,其實從來沒有一句是虛的……”
到了陳家,一家人起身相迎,讓到上座坐下,還沒等問問題,楊姨就一擺手:“我都知道了,把小陳的一件貼身常用的東西拿過來。”
陳正有兩個品相很好的核桃,整天在手心里搓過來揉過去,弄的油光錚亮。
楊姨拿出一只碗和一只香爐,倒上一碗清水,放上三只筷子。然后寫了一張符,燒成灰放入清水中。筷子斜著插在水里。楊姨把核桃放在碗里沾了沾水,擺在碗前面。燒了三炷香,舉著香作了三個揖。恭恭敬敬的插在香爐里。
楊姨點了一支煙,抽了一口,目光一瞬不瞬的盯著三炷香的香灰。突然,兩邊的香噗啦一聲同時冒出了火頭。楊姨把煙一扔,閉上眼,嘴里念念有詞,一會功夫,奇跡出現了:只見那三只筷子,慢慢的站了起來!眾人面面相覷,都覺得不可思議。
楊姨在說話,但是沒有聲音。
等到三炷香燒完,筷子一下倒了下去,楊姨也渾身一哆嗦,跌坐在沙發上。
陳正的父親給她端來一碗茶,楊姨喝了口茶,看向兩個油光錚亮的核桃,臉上的表情陰晴不定。
陳正的父親小心翼翼的問:“大師,情況怎么樣?”楊姨緩緩的說:“找不到他,……你家,”她轉頭看向范麗麗,:“可能被人下了咒。”范麗麗反應過來,驚恐的問:“我家?怎么回事?”
楊姨:“是祝由十三科的咒語。你買二手房,陳正看見那個往井里看的女人,都是它在起作用。而且……”她遲疑著,說:“不但給你們家下了咒語,還配上了,無比惡毒的東西……”她不說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,丁一急促的問:“楊姨,你就別賣關子了,快和我們說,那東西到底是啥?”
楊姨沉吟一會,說出的東西讓所有人大吃一驚:“尸粉。”
范麗麗呆愣良久,才問出一句:“是誰這么狠毒,要這樣害我和陳正?”
楊姨:“如果沒有目的的就為了害人,我就可以對付得了,但事情好像沒這么簡單。你好好想想,有沒有得罪什么人?”
范麗麗想了一會,說:“也沒記得有什么事啊,難道是陳正得罪的人?他在局里,這事應該是不可避免。”
楊姨說:“不是他的事,你仔細想想,有沒有對不起別人的事?”
范麗麗想了一會,說:“沒有吧……”雖然她說沒有,我們都聽出了她并沒有斬釘截鐵的否定。
楊姨:“好好想想。可不能遮遮掩掩的,舉頭三尺有神明……”
范麗麗遲疑著說:“難道是那件事?”幾個人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。
8
她接著說:“兩年前的那天晚上,我們院里來了兩個孕婦,一塊來的,那晚就是我自己一個醫生值班,其余都是護士,兩個孕婦的家屬一個給了兩千塊錢的紅包,你知道很多醫院都收紅包,這也沒什么好隱瞞的。特別是接生和動手術,那一個是婆婆陪著來的,沒給紅包。
結果兩人幾乎同時破了羊水,我只能給一個接生,我就讓護士把那個給了紅包的推進手術室,讓那個再等等,我想很快給這個接生后,馬上接生另外一個,沒想到,出來的時候,那個竟然走了,護士說去了另外一家醫院,后來家屬來鬧,才知道那個孩子沒保住,院長也是跑了很多關系才把這件事擺平。”
楊姨長嘆一聲,說:“不確定是不是她那邊,如果是他們的話,應該是她的丈夫或者是父親。”范麗麗說:“當時鬧得時候她的丈夫沒來,聽說是出海做船員沒在國內。”楊姨:“嗯,明天丁一先去院里,查查她家的信息,再去局里找陳正的同事,查查她家的情況,住在哪兒,都弄明白了,咱們再商量怎么辦。”
第二天,我和丁一趕到醫院,調查了那家人的所有情況,下午又接上楊姨,到了陳家。
范麗麗已經好幾天不去上班了,這時候心情很不好。到了之后,陳正的父親沏上茶,幾人喝了一杯,丁一就拿出手機,把復制的那家人的資料給楊姨看,那家人是嶗山區一個村子里的,公公婆婆賣早餐,蒸包,媳婦(當時去范麗麗醫院的孕婦)在一家私企上班,丈夫出海兩年回家一次,日子并不是很寬裕。
楊姨看完把手機遞給范麗麗:“你看看當時是不是這家人。”
范麗麗剛接過手機,立刻臉色就變了。
結結巴巴的說:“這個男的,這個男的……”丁一過去,看見范麗麗指著那個女人的丈夫,說不出話來了。
好久才從牙縫里擠出一句:“這個男的是我們醫院去年剛招的保安……”丁一和楊姨對視一眼,點了點頭。
應該就是他了。
9
楊姨問范麗麗:“這個人還在你們醫院上班嗎?”范麗麗點了點頭。
楊姨說:“他之所以沒離開醫院,可能是想看看你們被報復之后的慘狀,再說,又沒有理由抓他。即使硬強的抓了他,也拿不出證據來證明他害人。”
楊毅沉吟了一會:“這件事,你也有錯,但從另一角度說,你也不是故意的,只是沒想到那么嚴重的后果。但對他來說,那是災難性的,無法接受。所以他處心積慮的想害你和你的家庭。他可能在值班的時候,悄悄地把尸粉(夭折的嬰兒加工而成)放進你的口袋,鞋里,或者是摻在你喝的咖啡里……”說到這里,只見范麗麗驚恐的睜大眼睛,一下沖進洗手間,干嘔起來。
楊姨過去,拿出一顆藥丸,讓她服下。范麗麗服下藥丸,才逐漸的平靜下來。
楊姨繼續說:“他可以用咒語把各種怨靈招到你家,也可以在你選擇房子的時候,左右你的決定。我懷疑那雙井底的繡花鞋,就是他放進去的。”
范麗麗滿腔怒火,憤憤的說:“這人也太狠了,直接想害死人啊,楊姨,無論如何你要幫這個忙啊。”
楊姨說:“嗯,先給他一個警告,你和陳正也被他報復的不輕了,如果他還一條道走到黑的話,咱們就只好下狠手了。”
10
第二天,范麗麗醫院的院長找那個保安談話。(這是范麗麗和他商量好的)我,丁一和楊姨趁機打開了他的儲物柜。里面有他的衣服,鞋襪和洗漱用具。在柜子的最里面,是一個手提包,打開手提包,里面竟然裝著一只塑料罐子,類似于存錢罐的那種。罐子的口緊緊的扎著紅布,奇怪的是,紅布中間被剪子剪開了,朝外翻著,留下了一個小口子。
楊姨和丁一交換了一下眼神,楊姨點了點頭,從口袋里掏出一個銅錢,用針扎破指尖,滴上幾滴血,從紅布上的口子,把銅錢放了進去。我仿佛聽見了一聲悶叫。楊姨用一個回形針把口子封起來,等了大約五分鐘。才把針取下來,打開口子,用手機的手電往里照。好奇心驅使我和丁一爭先恐后的朝罐子里看。
等看清里面的東西,兩人不禁渾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:那是一只被烤干的的貓尸,蜷縮在罐子里,縫隙里填充著大米。
楊姨用一只鑷子把銅錢取出來,把罐子按照原樣放好。又把他的柜子整理了一下,才和我倆離開。
兩天之后,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。保安了,用一種決絕的喝下一整瓶百草枯。據說痛苦掙扎了一個上午才斷氣。
丁一打把消息告訴了楊姨。在里,丁一對楊姨說:“保安也挺慘,家里還有父母和老婆,……這事是不是可以畫個句號了?”楊姨說:“沒想到這個人這么鉆牛角尖,本來是想把他的邪術給破了,他能收手作罷,沒想到他竟然這樣……這事情更難辦了。從他行事的來看,不僅僅是范麗麗,只怕是咱們也要有麻煩了……”接著叮囑丁一再畫幾張符給范麗麗送去。
沒想到,隔了一天就出了意外。
那天晚上,約摸十一點多,范麗麗給丁一打來了,我和丁一的床對著頭,雖然沒有貼在聽筒上,但還是聽到了范麗麗在里既驚恐又絕望的尖叫:“啊——快來!丁一,那個保安從窗戶往屋里爬……”
11
等我和丁一接上楊姨,趕到陳家,范麗麗已經被送往醫院,陳正的母親摟著孫女在客廳里發呆。
據她說,他們聽見范麗麗在房間里尖叫,等到打開門,才發現范麗麗已經從樓上跳了下去。他們住的是三樓,她和陳正的父親跑到樓下,范麗麗已經昏迷不醒,陳正的父親叫了幾個鄰居,把她送去了醫院。
楊姨和我倆一起趕往醫院,找到范麗麗的病房,看到她,幾個人都覺得事情不妙。
只見范麗麗臉色鐵青,緊閉雙眼,嘴角往外泛著白沫,陳正的父親用餐巾紙不停的給她擦拭。范麗麗似乎沒有任何知覺,直挺挺的,一動不動。陳正的父親說了范麗麗的傷勢。左腿粉碎性骨折,右腿也是骨折,不過情況稍好點。人已經陷入重度昏迷。
楊姨臉色凝重,示意陳正的父親給換個單間病房,陳正的父親去交涉了很長時間,院方才同意,還額外加了二百塊錢。
楊姨指著范麗麗的脖子,對陳正的父親說:“這里有東西,得先把這個東西拿出來,不然就算是傷治好,人也醒不過來了。”老陳問:“是什么東西?”楊姨:“很小的東西,具體是什么,也看不大出來。”說完從包里拿出一個薄薄的刀片,在范麗麗的咽喉處割了一個小口。只見一塊尖尖的東西露了出來,竟然是一截貓的爪子。楊姨用一個小鑷子夾出來,放在一塊手帕上。對陳正的父親說:“就是這個東西作怪。只要拿出來用符水破邪,小范才不至于有危險。”陳正的父親連忙道謝,請楊姨盡快施法。
楊姨要伸手去包里拿東西,突然停止了動作,側著耳朵聽。走廊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,和熙攘的說話聲。
回頭往病房門看去,只見幾個警察趴在門玻璃上,示意屋里開門。丁一看了看楊姨,楊姨點了點頭。
打門,幾個警察徑直走到楊姨面前,其中一個語調平和的問楊姨:“你是楊桂芬嗎?”楊姨:“我是楊桂芬,你們有什么事?”我才知道楊姨全名是楊桂芬。
警察看了一下范麗麗,發現了被楊姨割開的脖子上的小口子。轉頭對楊姨說:“楊桂芬,有群眾舉報你非法行醫,大搞迷信活動,看來所言不虛啊。走吧,跟我們去局里協助調查。”我們幾個面面相覷……
陳正的父親站起來對幾個警察說:“我是市局陳正的父親,是我要求她給我兒媳婦診治的。”
其中的一個說:“陳正,我認識他,但這個事有群眾舉報,我們就得調查啊,這樣,我們先帶她回局里,爭取盡快調查清楚。”
楊姨收拾了一下包,對陳正的父親說:“沒事,我跟他們去。丁一,你照顧好你表嫂。”
一行人送楊姨下樓,快出醫院門的時候,楊姨突然站住了,只見她回頭朝病房樓看,幾個人也一塊回頭向病房樓看去,只見一個護士站在病房陽臺上,看到我們回頭,匆忙離去。
12
第二天,從市局得到消息:楊姨因為無執照行醫,拘留兩個月。
我和丁一立刻去探視她,托了關系,好不容易才見到楊姨。楊姨一見我和丁一,就急促的對丁一說:“醫院里有一個護士被保安附了身。我就是被她舉報的,她還會隨時對范麗麗下手,你告訴陳正的父親,讓他多幾個人輪流看護著她。……還有,”楊姨停了一會,繼續對丁一說:“要盡快找到陳正,他正在遭受非人的折磨……”
我和丁一驚訝的說不出話來。
良久,丁一問楊姨:“我只會簡單的東西,這些事我都應付不了啊……”
楊姨:“再去找找老袁。”丁一:“找了他好幾次了,他都不愿意出面。”楊姨:“一時一時,情況已經很危急了,再說,不去找他,還有更好的辦法嗎?”
丁一答應了。從拘留所出來,他先給陳正的父親打去,告訴他范麗麗那邊不要離開人。然后撥通了老袁的,沒想到老袁竟然接了,他讓丁一抽空過去他那邊。
還抽啥空啊,丁一和我一刻不停,立即開車直奔城陽。
看到老袁,我和丁一氣就不打一處來,只見他躺在幾個打撲克的人身后的一個角落里,翹著二郎腿,磕著瓜子,悠然自得。
丁一氣的要揍他,被我拉住了。
老袁也斜著眼,瞟了丁一一眼,嘿嘿樂了:“小子,知道我為啥嗑瓜子不?”
丁一不系理他,我連忙打圓場:“嗑瓜子對臉部肌肉有好處唄……”
老袁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空煙盒,搖了搖頭,:“不對,不對,是因為沒煙了。”
哦,原來是這樣!我也不管丁一了,飛奔到最近的商店買了兩條哈德門煙,疾步如飛的回來,恭恭敬敬的遞給他。
丁一怒火逐漸平息,,等他點上一支煙,把事情大體跟他說了一遍。
老袁聽完后,對丁一說:“嗯,事情可能是無意中造成了嚴重的后果,你報過來,我報過去,只會越來越狠,這樣吧,”他把扔在地上的空煙盒扯成兩半,從口袋里拿出一支記號筆,在兩個煙盒蓋上分別寫了幾個字,給了丁一。
接著叮囑丁一:“回去以后,在范麗麗病房門口把這個”他指著其中的半邊煙盒,:“燒掉。然后,在范麗麗的床頭放上一碗清水,兩只筷子十字交叉,一只放在另一只上面,如果一晚上筷子不動,就沒事了。如果筷子動了,掉下來,那就是不行,事情還不干凈。”
他看了丁一一眼:“把手伸過來。”丁一把煙盒裝進口袋,伸過手去。老袁在他手心里寫了一個繁瑣的字,好像是幾個字疊加起來的。
老袁寫完叮囑他不要洗手,把符字保護好。到時候有用。至于怎么用,老袁附在丁一耳邊,輕聲說了幾句。
接著又說了另外一半煙紙的作用:醫院里所有的事處理完以后,去陳正的房子那邊,把一套陳正的衣服或者鞋子和煙紙一塊燒掉,不久陳正就會出現……
當晚,我和丁一吃了點飯,趕往范麗麗的病房。按照老袁說的,支走了病房里的人,只剩下陳正的父親老陳。丁一找了一個不銹鋼小盆,把煙盒點上,放在里面。
三人看著煙盒燒成灰燼,我伸手去拿,想把東西處理掉,丁一卻低聲把我喊住了:“于得水,先別動,等一會。”我回過頭去看他,卻發現他的目光呆呆的望著病房外面。我順著他看的方向看去,頓時覺得渾身冰涼:只見一個一身工裝的女護士躲在黑暗中,透過門上面的小玻璃口,注視著我們……
看到我們看向她,扭頭走了。
等到我和丁一打開門沖出去,走廊里早已不見她的蹤影。
當天晚上,丁一在范麗麗的床頭放了一碗清水,依照老袁說的,把兩根筷子放在碗上成十字形,穩定住。然后出去給老陳買了盒飯,老陳吃完,三人一起守夜,如果能平安過得了今晚,那基本就沒什么問題了。
但是,出現了老袁預測的第二種情況,晚上過了午夜,我盹的實在睜不開眼,就到旁邊的床上趴著,準備迷糊了一會。丁一卻使勁推了我一把,我一下子抬起頭,就看到了令人吃驚的一幕:只見那只在上面的筷子慢慢的傾斜,最后啪嗒一聲貼著碗沿掉在地上。我和丁一都知道事情沒有擺平,還有更兇險的事情要發生。
不過令人意外的是,接下來一連幾天卻平安無事,范麗麗也蘇醒了過來。精神萎靡不振,很虛弱,腿部的疼痛折磨著她,看起來很憔悴。
傷勢稍微穩定一點,她就問丁一陳正找到沒有。看到丁一搖頭,她不禁痛苦的閉上眼睛……
丁一也夠受的,好幾天沒洗手了,小心翼翼的保護著老袁畫在他手心的符,像呵護寶貝似的。
我倆一塊去查過護士的資料,也沒發現有哪個護士異常,想先發制人也無處下手。
又到了晚上,丁一決定不管醫院這邊的事怎么樣,先去陳正家那邊,燒掉老袁寫的另一張符。看看能不能找到陳正。
我和丁一草草吃了晚飯,去陳正父親家找了一雙陳正穿過的鞋子,把老袁寫了字的半邊煙盒放在里面,去了那晚陳正失蹤的拆遷區。
丁一點上三炷香,用土栽住,嘴里念念有詞。等香燒完,拿出陳正的鞋子,用火點著。鞋子是化工材料做的,很容易燒著,并且有一股難聞的味道。鞋子直冒黑煙,煙盒也燃燒殆盡。
我倆背靠背坐了足足兩個鐘頭,又起來四處找了很久,也沒找到陳正。倆人不禁同時對老袁的本事產生了懷疑。
猶豫中,陳正的父親打來,讓我們立刻趕回醫院。我和丁一面面相覷,顧不上多說,驅車直奔醫院。
我開著車,丁一坐在副駕駛上,給老袁打了。原原本本的把所有的事跟老袁說了。
老袁聽完,沉默一會,突然連聲說:“壞了壞了,壞了壞了。壞事了。”丁一張口結舌,說不出話來,不知道老袁說的是什么意思。老袁繼續說:“哎呀,丁一,你把兩張符燒反了!在病房那張,應該在小陳失蹤的地方燒!你剛才燒的那張,應該在范麗麗的病房里燒!你可算把事辦壞了!……唉,也算是天意啊。那邊也是兩條人命……丁一,你趕緊去醫院,別忘了我對你囑咐的事,救你表嫂。你表哥,大約是找不回來了……”
丁一還想再問他,他已經掛了。
13
我和丁一趕到醫院,只見幾個醫生在搶救范麗麗,范麗麗臉色煞白,口吐白沫,眼睛使勁往上翻。只看見大片的白眼球。陳正的父親在一旁嚇得直掉眼淚。
丁一把他拉到旁邊,詢問了一下,才知道,剛才范麗麗睡了,老陳也趴在病床上打盹,朦朧中,看見一個人進來,去病房櫥里拿了一件衣服就走了。結果范麗麗很快就痛苦的起來,把他吵醒了,只見范麗麗一邊,一邊顫抖,吐白沫,人看著一會不如一會。
丁一急得滿頭大汗,直接找到了醫師,詢問他今晚有哪個護士值班沒到這個房間里來,或者是不該值班的護士,主動值班,有沒有護士行為異常。醫師想了一會,說:“倒是有個護士小林,剛才來了,說路過醫院上來看看,別人都是正常值班的,沒什么特別的。”我和丁一,醫師,老陳趕到值班室,值班室的護士說,小林去了儲物間,說想拿自己的水杯,回家刷洗干凈。
幾個人趕到儲物間,發現門從里面反鎖。丁一二話不說,一腳把門踹開了。里面的場景實在令人震撼:只見那個叫小林的護士,雙眼發直,手里拿著一件衣服,(應該是偷拿的范麗麗的衣服)一邊扯拽著,一邊用牙的撕咬,嘴角竟有絲絲血跡。幾個人呆愣著,看著小林把范麗麗的衣服撕爛。丁一用手勢示意我們幾個不要慌,然后緩緩走到小林旁邊,用老袁給他寫了符的那只手,輕輕的拍了拍小林的肩膀,嘴里嘟囔了一句:“就這樣吧……”話音未落,就聽見小林發出一聲我們從未聽過的慘叫……
14
小林倒在地上,幾人七手八腳的把她抬進病房,她的同事給她打上吊瓶,不久她就醒了過來。醒來問她最近發生的事情,十問九不知。
范麗麗也恢復了正常,兩個月后,身體能活動了,老陳的父親給她辦理了出院,粉碎性骨折的腿由于傷勢太重,留下了殘疾,走路一瘸一拐的。丁一,我,陳正的父母,派出所的警察,都沒停下尋找陳正,但是直到發文,陳正仍然沒有找到。
楊姨蹲滿兩個月,也被放了出來。后來和她說起這件事,她直言以后可得小心,再做事一定要做的嚴密,不能再被人抓住把柄。至于丁一燒錯的那半只煙盒,楊姨這樣說:“袁師傅給你的在范麗麗病房里燒的是鎮邪的,在拆遷區燒的是招魂的,你想想,你在拆遷區燒鎮邪的符,你還能找著陳正嗎?話說回來這或許是天意!就算是老袁,也不敢逆天而行……”
后來我和丁一又去城陽找老袁,卻沒找到他,聽說去了別的勞務市場,手機也換了號,他那副眼鏡,丁一一直保存著。
(全文完。墻壁女尸案請關注下一篇::燈下姻緣)
關注,評論哦